逃避统治的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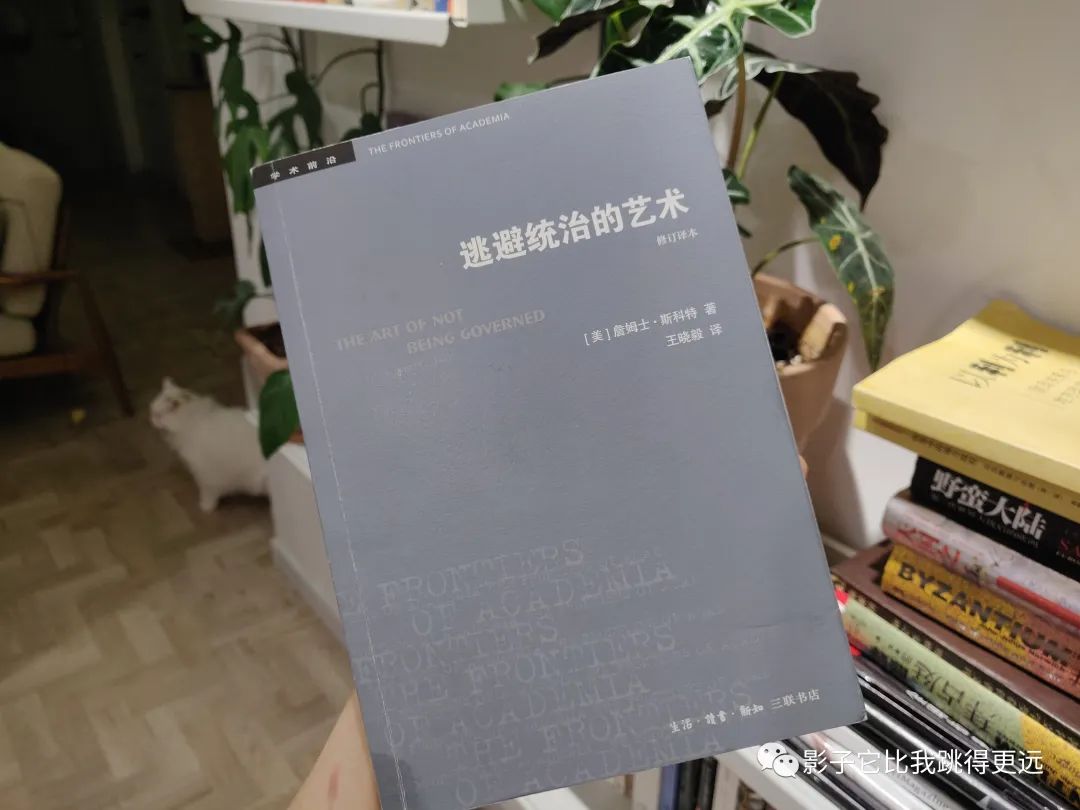
多年前读过一本影响了我民族观念的书《华夏边缘》,苦于没有进一步延伸的阅读方向,就搁置了,斯科特这本完全写到我的心坎儿上!
一个民族到底如何定义?它与别的民族之间是以什么为标准划分?是语言?是传统?是生活的区域?是生活习惯?是宗教?
如果把少数民族看做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以血统为脉络的分类方式,上述这些疑问完全得不到合理的解答。在试图厘清历史脉络和划出界线的时候会发现,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斯科特给了一个更合理的说法:少数民族是在一轮又一轮逃避核心国家统治的过程中动态变化的。
如果用这种涟漪式的动态观点来看待民族,很多问题都说得过去了。
“原始”“野蛮”未开化“的族裔为什么很难独立建国?中华思想会解释为没有文字、没有成熟的政治制度等等,但是跳出这种沙文主义的傲慢,可能归根结底因为他们争取的根本不是一种以国家为中心的权利,他们争取的是一种不被统治的权利,是自由的权利。
这种斗争在现代政治上很难成功,在现代国家主义范围内,这种诉求是没有空间的。
独立可以解决问题吗?可能也不行,因为争取的就是不统一、不合作、不被管理,争取的是一种国家主义以外的自由。
或许现代国家的民族矛盾之所以表现激烈,是因为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帮助下,国家权力深入地抵达偏僻的角落,人已经失去了逃离和退却的空间。
各国最近除了开始对南极大陆打起主意,连月球上的土地都开起会瓜分了。
你或者在这个国家,或者在那个国家,或者被这个政府管理,或者被那个政府管理,无主之地不复存在,开拓新的土地成为自由民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
而人类逃避现实的需求永远存在,鲁宾逊、桃花源、香格里拉…现代社会里,这种逃避只能用商业化的旅行来短暂而虚假的实现。
前现代社会,塞上牛羊是一种可实现的逃离,而现代世界,连游戏里都得还房贷。
资本主义是如此彻底的颠覆了人类世界啊。
酒吧长谈

2010年左右看了很多本略萨,没留下什么太深的印象,眼看风头紧赶紧买了本盗版……怎么改革开放四十年了,又开始打地鼠式看书了。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啊朋友们!
我们为什么需要多维度多视角的文本记录?
略萨在序言里写道:“每个印加帝王登上宝座时,都伴有一批学者,他们负责修改历史,以表明印加的历史是在现今帝王的统治下才达到高峰的,其先帝们的一切丰功伟绩就都归功于他了。结果是,要想重新恢复被神秘地歪曲了的历史,就成为不可能的了。”
人类的记忆实在太容易被修改了,几个月之间就能天翻地覆。
多视角的记录,每一份都值得珍惜,那些片段化的、甚至不客观的、情绪化的,都在修正“官方的”、“有目的性的”、“被审查的”、“最终定论的”历史文本。
嗯,每一份记录都值得。
伊斯坦布尔三城记

伊斯坦布尔,我的生命之光,我的梦想之城,我反反复复在不同的影片和文本中咀嚼它,我对它永不厌倦。
它是我的诗歌,我的咏叹调,我的海洋与草原,我的星空与森林。
古希腊与古罗马在此交汇,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此争夺不休,它是我探查前现代社会的窗口,是我试图理解世界秩序变幻的百科全书。
以城市变迁为脉络的书籍在欧美通俗历史中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类别,光我自己随便就看过《耶路撒冷三千年》、《罗马》、《西西里史》,还有关于伊斯坦布尔的若干。
按时间线从头写起的问题是,有些时间段可供对照的记录文本不够多,就很难说出新花样来,按部就班略显无聊。
不知道为什么国内没有兴起这类图书,史料丰富详实不是我们的优势吗?怎么没人写。
最近开始看拜占庭三部曲,视角不同,就很有意思。
如果站在基督教本位的视角来看,1453年是“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是文明的完结,是基督教之殇;在伊斯兰教的位置来看,则是“伊斯坦布尔大征服”,是伊斯兰文明的高光时刻。
那站在一个局外人的角度来看,又是什么呢?
对同样历史事件反复的、不同角度的叙述和解读,会修正狭隘的观点,书中自有天地呀。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

又是一本盗版书,怎么回事儿。
这本书的田野对象是几个华北东北地区的村庄,探讨了农村经济和政治改革对村庄造成的影响,包括社会分层变迁、家庭结构变化、女性话语权上升和父权制度衰落。
回溯我国个体化的过程,跟西方的个人主义兴起是不同的。
西方是主动的、自下而上的抗争,个体经济和人格上从家庭摆脱出来,进入公共领域,同时伴随了强烈的政治诉求。
而中国是自上而下的集体化,国家推动个体从家庭进入国家为唯一主导的情境,这种个体化过程伴随的是对国家集体的无条件服从,并不被鼓励在公共领域争夺主导权。只有在私人领域,这种抗争才是被允许的,这种个体化是失衡的。
我们的个体化发育就必须这样残疾着吗?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

终于有人展开讲一讲农民社会经济学了!真是久旱逢甘霖啊!
在对小农思想的批判中,一直的说法是:“安于现状”、“谨小慎微”、“没有冒险精神”、“浑浑噩噩”,这种充斥着精英式的傲慢话语既让我不太爱听,主要是,我从来没下过乡,缺乏生活经验,根本不知道怎样理解。
作者提到一个比喻来描述农民的生活境况:“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
小农经济社会中,农民对于“剥削”的忍耐度主要取决于“我能剩多少”,而不是“你拿走多少”,在这个前提下,固定比例和固定数量的税额在丰年和灾年对于农民的生死存亡有着不同的影响。
在前现代社会中,农民对地主剥削的容忍,伴随的是地主承担起社会责任,必须履行一部分道德义务,这是剥削阶级为经济不平等辩护的理由。
所以在灾年的时候,富人必须承担起“减免税收”、“开仓放粮救灾”这样的义务。
农民为了这样的生存保障才会愿意在丰年和平年时缴纳税赋。
这个平衡是非常微妙的,如果地主不承担最低生活保障的义务,就会变为“为富不仁”,失去权力合法性,农民抗议和造反就有了道德依据。
进入殖民经济时期,土地拥有者不居住在当地,税收强度变得没有弹性,对于公共土地(森林、湿地)的强行占有使农民的灰色收入又减少了,而土地拥有人居住在遥远的城市甚至国度,在灾年来到的时候,不再承担社会责任了,阶级契约大规模崩溃了。
一个不承担最低生活保障的课税主体在道义上是说不过去的,社会下层不参与到政治生活中的前提就是政治精英保障他们的生存,如果这种保障发生了故障,排除社会下层、独揽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就失去了重要支撑。
权利和义务就是得对等。
再说下去又得炸了。
猫然而止!

iker
Share post:
逃避统治的艺术
多年前读过一本影响了我民族观念的书《华夏边缘》,苦于没有进一步延伸的阅读方向,就搁置了,斯科特这本完全写到我的心坎儿上!
一个民族到底如何定义?它与别的民族之间是以什么为标准划分?是语言?是传统?是生活的区域?是生活习惯?是宗教?
如果把少数民族看做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以血统为脉络的分类方式,上述这些疑问完全得不到合理的解答。在试图厘清历史脉络和划出界线的时候会发现,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斯科特给了一个更合理的说法:少数民族是在一轮又一轮逃避核心国家统治的过程中动态变化的。
如果用这种涟漪式的动态观点来看待民族,很多问题都说得过去了。
“原始”“野蛮”未开化“的族裔为什么很难独立建国?中华思想会解释为没有文字、没有成熟的政治制度等等,但是跳出这种沙文主义的傲慢,可能归根结底因为他们争取的根本不是一种以国家为中心的权利,他们争取的是一种不被统治的权利,是自由的权利。
这种斗争在现代政治上很难成功,在现代国家主义范围内,这种诉求是没有空间的。
独立可以解决问题吗?可能也不行,因为争取的就是不统一、不合作、不被管理,争取的是一种国家主义以外的自由。
或许现代国家的民族矛盾之所以表现激烈,是因为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帮助下,国家权力深入地抵达偏僻的角落,人已经失去了逃离和退却的空间。
各国最近除了开始对南极大陆打起主意,连月球上的土地都开起会瓜分了。
你或者在这个国家,或者在那个国家,或者被这个政府管理,或者被那个政府管理,无主之地不复存在,开拓新的土地成为自由民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
而人类逃避现实的需求永远存在,鲁宾逊、桃花源、香格里拉…现代社会里,这种逃避只能用商业化的旅行来短暂而虚假的实现。
前现代社会,塞上牛羊是一种可实现的逃离,而现代世界,连游戏里都得还房贷。
资本主义是如此彻底的颠覆了人类世界啊。
酒吧长谈
2010年左右看了很多本略萨,没留下什么太深的印象,眼看风头紧赶紧买了本盗版……怎么改革开放四十年了,又开始打地鼠式看书了。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啊朋友们!
我们为什么需要多维度多视角的文本记录?
略萨在序言里写道:“每个印加帝王登上宝座时,都伴有一批学者,他们负责修改历史,以表明印加的历史是在现今帝王的统治下才达到高峰的,其先帝们的一切丰功伟绩就都归功于他了。结果是,要想重新恢复被神秘地歪曲了的历史,就成为不可能的了。”
人类的记忆实在太容易被修改了,几个月之间就能天翻地覆。
多视角的记录,每一份都值得珍惜,那些片段化的、甚至不客观的、情绪化的,都在修正“官方的”、“有目的性的”、“被审查的”、“最终定论的”历史文本。
嗯,每一份记录都值得。
伊斯坦布尔三城记
伊斯坦布尔,我的生命之光,我的梦想之城,我反反复复在不同的影片和文本中咀嚼它,我对它永不厌倦。
它是我的诗歌,我的咏叹调,我的海洋与草原,我的星空与森林。
古希腊与古罗马在此交汇,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此争夺不休,它是我探查前现代社会的窗口,是我试图理解世界秩序变幻的百科全书。
以城市变迁为脉络的书籍在欧美通俗历史中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类别,光我自己随便就看过《耶路撒冷三千年》、《罗马》、《西西里史》,还有关于伊斯坦布尔的若干。
按时间线从头写起的问题是,有些时间段可供对照的记录文本不够多,就很难说出新花样来,按部就班略显无聊。
不知道为什么国内没有兴起这类图书,史料丰富详实不是我们的优势吗?怎么没人写。
最近开始看拜占庭三部曲,视角不同,就很有意思。
如果站在基督教本位的视角来看,1453年是“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是文明的完结,是基督教之殇;在伊斯兰教的位置来看,则是“伊斯坦布尔大征服”,是伊斯兰文明的高光时刻。
那站在一个局外人的角度来看,又是什么呢?
对同样历史事件反复的、不同角度的叙述和解读,会修正狭隘的观点,书中自有天地呀。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
又是一本盗版书,怎么回事儿。
这本书的田野对象是几个华北东北地区的村庄,探讨了农村经济和政治改革对村庄造成的影响,包括社会分层变迁、家庭结构变化、女性话语权上升和父权制度衰落。
回溯我国个体化的过程,跟西方的个人主义兴起是不同的。
西方是主动的、自下而上的抗争,个体经济和人格上从家庭摆脱出来,进入公共领域,同时伴随了强烈的政治诉求。
而中国是自上而下的集体化,国家推动个体从家庭进入国家为唯一主导的情境,这种个体化过程伴随的是对国家集体的无条件服从,并不被鼓励在公共领域争夺主导权。只有在私人领域,这种抗争才是被允许的,这种个体化是失衡的。
我们的个体化发育就必须这样残疾着吗?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
终于有人展开讲一讲农民社会经济学了!真是久旱逢甘霖啊!
在对小农思想的批判中,一直的说法是:“安于现状”、“谨小慎微”、“没有冒险精神”、“浑浑噩噩”,这种充斥着精英式的傲慢话语既让我不太爱听,主要是,我从来没下过乡,缺乏生活经验,根本不知道怎样理解。
作者提到一个比喻来描述农民的生活境况:“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
小农经济社会中,农民对于“剥削”的忍耐度主要取决于“我能剩多少”,而不是“你拿走多少”,在这个前提下,固定比例和固定数量的税额在丰年和灾年对于农民的生死存亡有着不同的影响。
在前现代社会中,农民对地主剥削的容忍,伴随的是地主承担起社会责任,必须履行一部分道德义务,这是剥削阶级为经济不平等辩护的理由。
所以在灾年的时候,富人必须承担起“减免税收”、“开仓放粮救灾”这样的义务。
农民为了这样的生存保障才会愿意在丰年和平年时缴纳税赋。
这个平衡是非常微妙的,如果地主不承担最低生活保障的义务,就会变为“为富不仁”,失去权力合法性,农民抗议和造反就有了道德依据。
进入殖民经济时期,土地拥有者不居住在当地,税收强度变得没有弹性,对于公共土地(森林、湿地)的强行占有使农民的灰色收入又减少了,而土地拥有人居住在遥远的城市甚至国度,在灾年来到的时候,不再承担社会责任了,阶级契约大规模崩溃了。
一个不承担最低生活保障的课税主体在道义上是说不过去的,社会下层不参与到政治生活中的前提就是政治精英保障他们的生存,如果这种保障发生了故障,排除社会下层、独揽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就失去了重要支撑。
权利和义务就是得对等。
再说下去又得炸了。
猫然而止!